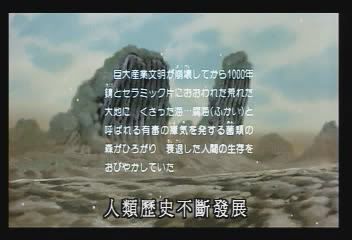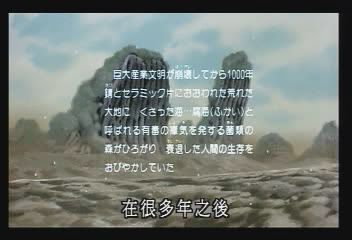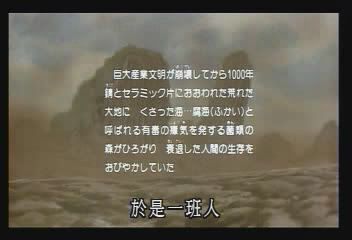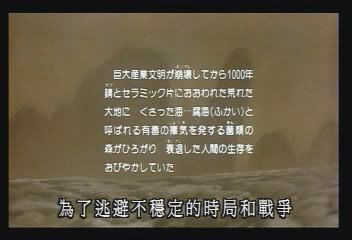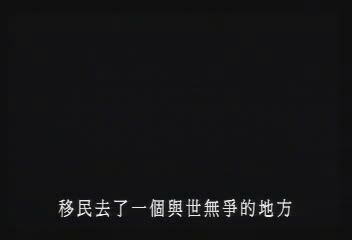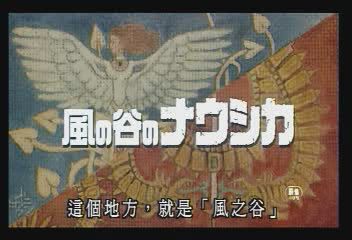這篇,正確的題目應該可以定為《關於幽波紋註記stand與stand-by之爭議》。
No!屁!沒什麼好爭議的,現在就是Stand而已。
不過永野護很喜歡改角色的名字,那麼一個從1868年明治時代活下來的荒木老師(冷)以後會不會改替身稱呼就不知道了。
會寫這篇,其實由來是上一篇在黑米引起了些許餘波盪漾的《日文的「隨便亂讀」文化》中,提到了幽波紋,林姊(elielin)(其實應該比我小,不過我先裝小一點好了)(其實我很尊敬她)跟我的意見有差異,所以有著小小衝突。
嗯,其實衝突不只「幽波紋」,不過這篇重點在幽波紋,不在別的,所以別的下次有空我再慢慢解釋好了。
我上一篇對於幽波紋振假名(振り仮名)為「スタンド」的解釋如下:
- 「ジョジョの奇妙な冒険系列中,荒木老師不用dummy而用stand,是因為幽波紋是一種精神能力,而精神能力高到一定的程度(應該要比三四樓還高很多,可能要十幾二十樓吧)之後能夠具體化,成為能替代本體行動的一種替身(standby),之後就簡稱為stand了。」
elielin(覺得再稱她林姊我會被丟拖鞋──就像包租婆那樣……愕,冰炫風…)覺得我解釋的不夠好,甚至亂解釋。所以我寫了這篇來說明。
先要聲明,第一、這不是回擊,只是很單存的解釋為什麼我用standby,而不直接用stand。第二、我上述對於「對於幽波紋振假名(振り仮名)為『スタンド』的解釋」很輕鬆帶過,是因為《日文的「隨便亂讀」文化》原文並不是只給看過《ジョジョの奇妙な冒険》的人看,我的解釋方式,目的在讓沒看過該部漫畫的人也看得懂《ジョジョの奇妙な冒険》大概是什麼故事,而且主題不是該篇漫畫,所以僅採用通俗的解釋而放棄專業解釋,這在討論串中也有提到。
接著,來看討論串中elielin對於幽波紋標註(当て字)為「スタンド」的解釋如下:
- 「幽波紋」為什麼旁邊標註為「スタンド(中譯:替身)」?
(1)命名者是第三部出現的阿布德爾(モハメド・アヴドゥル)。
對於這樣「由生命能源所幻化的影像(vision)」,
因為它們總是『站在人的身旁』,
所以阿布德爾用英文的「Stand(片假名表記:スタンド)」為其命名。
他雖然是印度人,但跟著美國籍的喬瑟夫(英國血統),所以用英文命名。
(2)漢字之所以記為「幽波紋」,
一般推測應該是為了與第一、二部中出現的「波紋」取得連貫性,
以加強「這是JOJO第三部」的感覺,
初期以後都以直接寫「スタンド」來表示居多,
而比較起來也極少使用「幽波紋」這個字眼
(也是因為之後的替身成因,
漸漸脫離一、二部中因為呼吸法而產生生命能源的概念)
「幽」則是來自「幽靈」(因為初期解釋,替身乃守護靈般的存在),
而承太郎也一度認為背後的星之白金是「惡靈」。
「スタンド」表記為「幽波紋」,
是有其在故事中的明確成因,以及漫畫連載時為了接續所作的設計,
並不是什麼作者想要讀者怎麼唸什麼的,你完全搞錯了。
上述我都非常同意。之後,elielin質疑我用standby的解釋毫無根據,是以中譯替身來擴大解釋進而倒果為因。
請不要把我當成是網路上謠傳只會打嘴炮的宅男,我是個御宅。
所以了,身為一個御宅,用任何典故都得有パロディ(Parody),於是我用standby當然必須有理由,不然就是我濫用,若我用錯了我就得道歉,這不手軟也不逃避的。我後來翻找了些資料,卻一時找不到,只好大略說明了為什麼用standby的理由:
- 依據荒木飛呂彥1990年在週刊少年ジャンプ第幾號我忘記的訪問:
替身(Stand-by)就是英文Stand by Me「站在我身邊」的簡寫,
在替身剛出現的時候,荒木老師確實是把他們設計一種憑依現象,
但是在繼續畫下去的時候,替身就成為主角們人格的能量分身,而不是外來的背後靈。
荒木老師原本有打算用副體Doppel Ganger/Double-goer(又稱並行者),但是讀音不夠強烈。
最後還是選擇了Stand的簡潔有力。
替身的概念來自於「精神念体」,因此是具有人格的象稱……
並且補充了這些:
- (沒記錯的狀況下)
1999年之前,替身之前都註記為Stand-by,之後才改為Stand
1998年CAPCOM出的第三部主題格鬥遊戲大型電玩機台,替身的血量條還是用Stand-by註記
1999年移植PS版的時候,改為Stand,之後都稱為Stand
這麼說好了,會用standby而不是stand一定是我看過,不過用腦海的印象真的說不過去。資料非找出來不可,但是別說1990年的日文漫畫雜誌,我想當年的少年快報也早就給人丟光了吧?
幸好,我想到我有夢幻逸品。終於找到了!
傻呼嚕同盟官方公定夢幻逸品《無名的書》
智庫鯨工作室編撰/出版(傻呼嚕同盟前身)

以及非同盟的夢幻中夢幻逸品《奇妙的漫畫體驗》(這個稱號是我自己加上去的)
J.T 寫的 - 奇妙的漫畫體驗

這兩本書都提到了《ジョジョの奇妙な冒険》這本書。
先看《奇妙的漫畫體驗》第252頁:
- 「據原作者荒木氏所言,所謂替身『Stand-by』就是英文Stand by Me的簡寫」中間雜話省略「其實,在替身剛剛出現的時候,作者的確是把他們設計成一種『憑依現象』,但,很快地,替身就成為主角們人格的能量分身,而不再是外來的背後靈了。」(跟我講的非常類似,看來我受這篇影響很大……?)
再來看《無名的書》第42頁:
- 「於是乎,因為某種奇異的緣分的共鳴,這些主角們身上的波紋氣功竟然都凝聚成為具有人格與特異功能的『守護靈』狀態之形式──『替身』(Stand-by)──!」本書第43頁介紹了第四部東方仗助篇。(單元作者:J.T.)
我們可以看到,J.T.都是用「Stand-by」而不是「Stand」,也就是在當年的漫畫與公開資料上都是稱為Stand-by。尤其在《無名的書》,故事已經進展到第四部的東方仗助篇,但是J.T.還是用「Stand-by」來稱呼。這個年代大約是所謂JoJo冒險野郎的早期年代。那個年代的漫畫是印Stand還是Stand-by我沒有印象,我的冒險野郎被我阿母給丟了。
但是,我相信,曾經參與智庫鯨(現傻呼嚕同盟)的J.T.會寫這樣的資料一定有根據。以現在傻呼嚕同盟的水準,也不會允許公佈沒有考察資料就隨便寫的文章,我想以前應該也是。如果當年只叫做Stand而沒有Stand-by,J.T.這樣寫,應該會先被談璞K才對。換句話說,J.T.撰寫時候他手上的資料很可能就是我所謂那本1990年不曉得幾號的《週刊少年ジャンプ》。
這也是我記憶中是先有「Standby」之後才改成「Stand」的原因,以上的資料也能證明我並不是從中文轉譯「Standby」過去胡亂瞎掰的,而是作者曾經這麼用。
接著,我們來看漫畫第三部第一話的圖:

房間內有吉他、遙控車、腳踏車、啞鈴……這就是當時被稱為「惡靈」的白金之星拿來的。我們必須注意一點,雖然白金之星可以穿牆,但是腳踏車等東西不行。這就是該訪問提到,原本是惡靈的設定,是一種憑依現象,之後才改掉的。替身正式命名是第二話,第一話都只稱惡靈。
在我那篇《日文的「隨便亂讀」文化》中,關於幽波紋的這件事情我其實寫錯兩個部分。其一就是荒木飛呂彥老師一開始用的是Stand-by而不是Standby,之後才改用Stand。(咦?為什麼我後來記對了?其實是拜大台電動所賜,當年繳了很多學費,努力回想才記得有一橫。)
其二就是我提到的Doppel Ganger我打錯了。原文是Doppelgänger,中間沒有分開,然後o下面應該還有一個點標示發音,我不會弄,然後a上面有兩點,這我搞定了。這個字意思是酷似者。(德華辭典126頁/五洲出版社)
提外話,穆罕默德.阿布德爾(モハメド・アヴドゥル)香港翻譯為「鴨都勞」,有人知道嗎?愕……鴨都勞Orz
如果elielin有閱讀到這裡,非常謝謝你的閱讀。
另外,至於我用的振假名(振り仮名)以及你一直提的標註(当て字),請容我過幾天再解釋。我完全認同你的說法,不然不會按推。只是,你以及純敏都誤會我的哏點了。
補充資料:漫畫第花京院典明對抗死神13(漫畫第18集)的替身時,在手臂上用刀子刻出BABY STAND的傷口,那麼STAND的稱呼應該是更早就出現才對。2007/12/12